利津,丢失黄河的恐慌(1999年“行走黄河”日记)
编者按
黄河宁则天下宁,黄河不靖则天下忧心。治理黄河,历来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。1999年5月10日至6月13日,人民日报社“行走黄河”采访组,逆黄河而上,就黄河流域的防汛、断流、污染、水土保持、生态建设、文化承续等课题进行采访活动,刊发了上百篇、十余万字的文字和约200幅图片。
20年后,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,人民日报社重启“行走黄河”大型融媒体报道,在“2019行走黄河”活动启动之际,人民网将“行走黄河采访日记”重新整理发布,以帮助网友更好了解黄河以及黄河治理情况。
他们永忘不了前年失去黄河的恐怖,每天清晨急急地奔到这里,看到的总是一张袒露无遗的河床,没有流水,没有波澜,没有黄河。一年365天,没有黄河的日子倒有226天!
1999年5月11日 星期二 晴 28-14摄氏度 山东东营-利津-广南水库 行程160公里
穿越利津渡口的黄河浮桥。说是浮桥,看去却像“粘”在河底一样,河水比昨天看到的即将入海的那几行“眼泪”多点儿,但仍是极浅,所以浮桥很是沉稳,车开在上面,没有晃晃悠悠的感觉。
采访利津水文站,这是万里黄河流入大海之前最后一个水文站,距黄河入海处约100公里。这是一栋紧邻黄河大坝的房子,清洁整齐,却显得有些萧索。办公室里空旷而简陋,可副站长高振武说,你们往上走就会知道,这里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已经是太好了。再说,我们比当地农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收入还高呢。这个水文站有21人,离退休有12人。每年的国拨资金仅够人头费,人均月工资大约500-600元左右。利津曾经戴过贫困县的帽子,至今也还不富裕。
我们随高振武走下高高的大堤,黄河流得有气无力,河床中更触目的,是一处处拱出水面的沙洲。高振武很沉默,望着他终日相伴的这条河,半晌吐出一句话:
“十几年前的黄河,不是这样子的。”
他叹了口气,又说:“不过今年算不错了,断流得到了控制,搁在前年、去年,这会儿是黄河最枯的时候,没有过流。”
他们永忘不了前年失去黄河的恐怖,每天清晨急急地奔到这里,看到的总是一张袒露无遗的河床,没有流水,没有波澜,没有黄河。一年365天,没有黄河的日子倒有226天!农民们浇不上麦子,欲哭无泪。人、畜缺水,油田减产,农田枯焦……山东黄河河务局调研室的宋传国,用一个“惨”字来形容当时的情景。
今年,黄河也曾在入海之前丢失过,那是2月6日,利津断流……越来越频繁的断流,让传媒吃惊,消息流传开来,中国人震惊了──这毕竟是黄河,毕竟是中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之一。经过对黄河水资源的统一调度,利津3月11日就恢复过流了。虽说现在用水仍然得小心而又小心,控制了再控制,毕竟河道里还找得水。
我们终于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滔滔黄河──这是莱州湾之畔的上南水库。
上南水库是黄河下游最大的一个人工水库,蓄的就是黄河水,总面积39平方公里。其烟波浩渺之状很近似于西湖。它的壮阔与黄河的细弱形成极大的反差。时不时地看到水鸟衔着阳光联翩飞过,翅尖掠过湖面时,划起一道道银光。因为这里冬季有天鹅栖息,当地人称天鹅湖。
天鹅湖极为澄澈,就想,原来黄河本可以这么清碧可人的。把黄河水引进水库之前,先要经过沉沙池的过滤,把黄土高原的泥沙沉淀掉,再让河水清亮亮地流入水库。沉沙池与水库相依相偎,然而一浊一清,泾渭分明。
一打听,东营有大大小小七八十个水库,丰水时蓄,枯水时用。有了它们,东营人才能熬过断流之苦。水,是东营人每天念叨的字眼。黄河是东营的命脉,东营人最大的忧患,是黄河永远断流。东营人最大的梦想,是南水北调能够实现,引长江水来救黄河。有了充足的水,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和每年扩张的土地资源的东营,将一飞冲天!
每年“两会“期间,正是黄河最容易断流的日子,东营的党政领导在北京心神不定,每天都往回挂电话,只问一句:“黄河还有水吗?”
是谁把黄河丢了?把黄河丢在哪儿了?
黄河口治理研究所所长程义吉对我们细细分析黄河断流原因。
黄河首次断流出现于1972年。“从那以后,断流就愈演愈烈,严重威胁到沿黄地区的工、农业和人民工作、生活。”
程所长进一步介绍:1972年以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,其断流特点并不相同。
80年代,其断流时间较短,而且是间歇式,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,对周边地区影响也不大。
80年代末至90年代,断流时间提早,由70年代的五六月份提前至二三月,且断流时间延长,不仅全年断流天数从70年代的平均七八天增加到90年代的平均100天左右,一次性断流持续时间更从一个月延长到两个月甚至3个月。同时,断流的区域也扩大,过去只在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地区出现,现在上溯到济南泺口甚至开封,也就是说,下游近800公里的地区全断。
那么,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呢?
程所长认为,主要有四,“但人为因素很大”。
其一,10年来黄河流域处于枯水期,降雨量下降,使黄河这条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河流更加雪上加霜。
其二,经济的发展造成沿黄地区用水量急剧增加。50年代的流域用水量为100亿立方米,70年代为200亿立方米,到90年代,流域用水量为300亿立方米,还在呈上升趋势。
其三,黄河流域上的大中小型水库多达3000多座,黄河年均降水量为580亿立方米,而水库总容量就达到510亿立方米。一些大型水库,每个水库的库容就达200亿立方米。黄河水被张开巨口的水库层层拦截,终成涓涓细流。现在世界上有一种趋势,过去修了大量水库的不少国家,开始慢慢拆除,他们认识到盲目建设水库有不少“后遗症”。
其四,用水浪费严重,这在宁蒙河段表现最甚。按我国规定,每1亩地用水为三四百立方米,但在宁夏、内蒙沿黄一段,已经超过1000立方米,全流域有效利用率仅在46%左右。既使是东营,在灌溉农业方面也仍沿袭大水漫灌方式。
对于以黄河为生命之水的东营,对黄河下游的山东来说,既要承受每年7-9月洪水倾泻而下所带来的防洪排涝问题,又要承受非汛期的断流之苦。黄河就是这样让人爱恨交加,水少了是痛,水多了更痛。
据程所长介绍,从1993年成立黄河口研究所至今,他们的研究重点就放在如何稳定流路(指黄河不再随意改道)、水资源管理等问题上。“过去黄河是‘十年河东、十年河西’,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做到百年内不改道,保障当地经济、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。”作为一个重要对策,东营建起了一座库容为1.14亿立方米的亚洲最大的平原水库,使丰水枯用、冬水春用,基本无忧。
他欣慰的是,近年来,黄河断流问题已引起上上下下的高度重视,今年全国政协的第一号提案便是有关黄河问题。他认为,一是要尽快出台《黄河法》,以立法形式统一规划,统一管理,使上中下游统一协调。二是要南水北调,以最终解决黄河水资源问题。
从他们的言谈中深深体会到,黄河之水是东营及其他下游地区的命根子,他们太怕太怕失去这个已经岌岌乎可危的命根子了。
这两天,除采访之外,北约轰炸我使馆是个最热门的话题。遇见的人几乎都迫不及待地要交流对事态的看法,表达愤怒之情。这仿佛是一种冥冥中的警示,海的那一边,是强凶霸道的美国,海的这一边,是黄河面临断流之痛── 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失血的民族,那样的话,我们凭什么与强权抗衡?
黄河曾经怒吼过,今天的黄河,我们能坐视它的吼声喑哑吗?
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
- 评论
- 关注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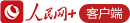




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 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
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