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海处的大河之恸(1999年“行走黄河”日记)
编者按
黄河宁则天下宁,黄河不靖则天下忧心。治理黄河,历来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。1999年5月10日至6月13日,人民日报社“行走黄河”采访组,逆黄河而上,就黄河流域的防汛、断流、污染、水土保持、生态建设、文化承续等课题进行采访活动,刊发了上百篇、十余万字的文字和约200幅图片。
20年后,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,人民日报社重启“行走黄河”大型融媒体报道,在“2019行走黄河”活动启动之际,人民网将“行走黄河采访日记”重新整理发布,以帮助网友更好了解黄河以及黄河治理情况。
●黄河入海口,黄河几乎见了底,河床上只剩下几行枯涩的“泪水”
●不敢再让孩子读这样的诗: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
●在这里,黄河每年为共和国新造三到五万亩土地,更新造了一个美丽的城市
●如果黄河从此只能遥望大海,中华民族的记忆是不是会无处搁置?
1999年5月10日 星期一 济南-东营-黄河入海口 今日行程420公里
多云转晴 偏北风三级 26-16摄氏度
自济南东行200余公里,到了东营。东营市的清洁美丽与幽静广阔,让我们很惊喜了一番。在东营市委宣传部崔相国科长的陪同下,我们直奔百公里开外垦利县靠近孤东的黄河入海口。
这里是万里黄河的终点,也是我们“行走黄河”的起点。
千百年来,黄河像一条来回打滚儿的巨龙,任性地选择它的入海之路。以郑州桃花崆为下游起点,就是因为那也是黄河没了峡谷的约束,开始打滚儿的起点。北到天津,南至江淮,这条大河蛮不讲理地忽然夺淮,忽然夺泗,忽然夺海河之路,甚而漫流四溢。它的每一次改道,都是华北、江北黎民的一次灭顶之灾。但是,它也滚出了一个一马平川、人口繁盛的华北平原;更以每年沉积三到五万亩土地的速度,滚出了一个年轻的黄河三角洲;滚出一个只有16周岁的少年城市──东营。
我们的脚下,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。
别处为人口众多发愁,这里却地广人稀,8053平方公里的面积内,只有170万的人口;别处为污染问题煞费苦心,这里的空气洁净度已达国际标准;别处为土地的日益减少而忧心忡忡,这里每年都在生长土地;别处在开发建设中为各种旧的“包袱”犯愁,这里却如一张白纸,让东营人精心描绘……
这里不久前还是渤海湾的一片汪洋,如今厚实的土地上已经此起彼伏地矗起胜利油田的钻机(俗称“叩头虫”)、铺出通向港口的高速公路,还有正在翻耕的农田……
而今,人们已经可以让黄河按人的意愿科学选择入海之途。按照一位治黄老人的说法,是“手牵黄河跟我走,让它咋走就咋走。”比如,发现某段近海大陆架埋藏着石油,就可以牵着黄河往这里走,待它淤满之后,才牵着黄河离去,人们可以从容地开采石油──石油的陆上开采,要比海上开采节省成本十分之一。
我们路过一个黄河故道大桥。桥下是芦草凄凄,残存的堤岸蜿蜒犹存,黄河曾经从这里走过,这是1976年以前的刁河口流路。崔科长说,人工改道需要上下游配合,上游水库下闸蓄水,令故道基本见底;那一次东营动员了2600辆小推车,千军万马上阵,另筑河堤,使黄河走入今天的清水沟流路。
再往前,蓦见大路两旁槐花如霜似雪,密密簇簇。一股浓香的花香引来无数蜜峰,养蜂人的帐篷就逍遥地安在槐树之下。宣传部的司机小刘说,他在河口当过八年兵,亲见这里曾经一刮风就黄土漫天,相隔数米之远,人都会像鬼影子一样。这大片的槐树林,都是这十来年人工植成的,终于挡住了风沙黄尘。
可是,走近黄河入海之处,我们欣快的心情顿时荡然无存。
三年前的秋天,由于“华东山海行”的采访也是从东营启程,当时我们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:“黄河口好大的风!吹得尘起云乱,芦花一片披靡,唯滔滔黄河凝滞不动,波澜不兴,像是沉沉地、缓缓地渗入海里去一般。”然而,今天的所见迥然不同!
黄河几乎全然见了底──踩在干涸的河床上,终于相信关于“黄河极有可能成为一条内陆河”的推断。我们将怎样对后人描述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壮阔?告诉孩子们,那只是一个很久以前的童话?
宽广的河床,如今只剩下丝丝缕缕的细弱小溪,显得那样楚楚可怜,像是一张干枯多皱的老脸上,流淌着几行苦涩的泪水。据说,就是这么一丁点水,还是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,上游在引黄、蓄黄时做出牺牲,手下留情,才让它跌跌撞撞地流到渤海之滨。当然,这里也在引黄。东营有广袤的土地,那是昔日海的家园,经多年来黄河淤积而成。非有黄河水灌溉,才能勉强耕种。我们看到的引黄闸,低低地开着闸门,将黄河水不绝如缕地引出。
崔科长遗憾地说:“水太少了,没法行船,不能坐船去河海交界处看看了──伏秋水大时,那情景真是壮观呢!”
我们默默地在黄河干爽的河底行走着,望着不远处黄河的归宿──大海,心中绞痛着:这就是黄河!?
折一根枯枝,想在河道上写几个字,可是几乎“写”不出,河底太干太硬了。
然而,到了黄河流入大海之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──利津水文站,副站长高振武却不无欣慰地说:今年很不错了,断流得到了控制,“往年这时候,一滴水都没有。”今年2月6日,利津断流,经过对黄河水资源的统一调度,3月11日就恢复过流了。虽说现在用水仍然得小心而又小心,控制了再控制,毕竟河道里还找得水。而东营人一提起就后怕的1997年,利津断流达227天之久!人、畜缺水,油田减产,农田枯焦……山东黄河河务局调研室的宋传国,用一个“惨”字来形容当时的情景。
“如果黄河成了不再入海的内陆河,东营将不复存在!”东营市经贸委主任李建业忧心忡忡。
一条曾经咆哮万里的大河,一条曾经流响千古的大河,会这样在入海途中凄怆地颓然而逝吗?那么,黄河下游的亿万生灵、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,岂不都成了无本之木?无源之水?
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
- 评论
- 关注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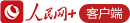




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 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
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